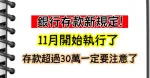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趙構為何56歲時主動退位,將皇位還給趙匡胤一脈,並不是因為高尚

3/3
這句話看似謙讓,實則留有餘地。
誰都知道,56歲不算老,精力也未見衰退。趙構是在做局,把「太上皇」的身份當成第二道護城河。
他退了,但並沒有走。他依舊住在宮中,依舊接見群臣,依舊干預軍政。
他把皇位交出去了,把權力的一部分拿回來。表面上風平浪靜,實則波濤洶湧。
趙昚很清楚這個局,他不上頭,也不反擊,按部就班當皇帝。
太上皇和皇帝兩套權力系統平行運轉,趙構贏得的是體面,也是主導權。
這個安排,至少維持了10年局勢穩定。可趙構知道,時間拖久了,終究會出事。
與其未來被驅逐、清算,不如提前設局、全身而退。他選趙昚,不是親情所至,而是博弈所需。
趙構退得早,只為避禍不為清名
趙構退位前夕,宮裡氣氛很怪,誰都看出不對勁,卻沒人敢說。
那是紹興三十二年,1162年正月,趙構宣布禪位,大臣反應出奇地快,奏章一片歡呼,說「太上皇高風亮節」,說「天命所歸」,說「萬民所盼」。
可真有人信這些?宮門之外,朝堂之上,人人心裡都清楚,這不是一場感情戲,是一場政治演出。
趙構退位有多快?快到不像話。
當天詔書一下,趙昚立刻登基,改元「隆興」。
所有儀式提前準備妥當。宮廷衛隊換防,后妃遷居,禮儀大臣一排排站好。一切都在計劃之中,半點不拖泥帶水。
趙構不是做戲,他是真的怕。
過去十多年,他活在各種刺痛里。建炎年間的軍變,韓世忠、張浚的跋扈,李綱的直言,岳飛的威望,這些人不是敵人,都是趙構心頭的影子。
他在這些「忠臣」身上看到了什麼叫「壓制不住的力量」。
尤其是岳飛。那場殺岳的風波之後,趙構明白,任何一個太有「理想」的人,都會威脅到皇帝的安全。
哪怕是真忠良,也不能留。岳飛走了,可朝野信任也崩了。
趙構從那以後,徹底認清一個現實:只靠皇帝的身份,是壓不住那些人心的。
所以他得退。退得早,退得快,退得乾脆。
趙昚不是岳飛,不是韓世忠,不是張浚,他沒軍權,也沒「北伐夢想」,趙構選他,看中的不是賢明,而是安分。
他知道趙昚不會逼宮,不會清算舊事,不會反咬一口。
趙構要的,不是交出權力,而是把「風險」轉移。
他繼續留在皇宮,仍被尊為「太上皇」,每日早朝前,大臣要先向太上皇請安。軍中重大調令,也要「御前通報」。
趙昚是皇帝,趙構是神,他退了身,卻沒退場。
這種結構,看似穩定,其實危險無比。因為它不是分工,而是牽制。太上皇不走,皇帝難大展拳腳;皇帝強硬,太上皇會幹預。
南宋政壇,進入一種「雙頭權力」的微妙狀態。
趙構也清楚,這種格局拖得越久,越容易出亂子。他必須一步步淡出,慢慢斷線,開始頻繁出行,搬離皇宮,搬去德壽宮,自稱「養病」,減少露面。
可他始終沒有徹底放手。直到去世前,他依舊保持對政局的某種掌控感。
哪怕是趙昚身邊的親信安排,他都有份插手。
趙構退位,不是清高,是清醒。他躲開刀口,卻死死捏住刀柄。
表面風光的「歸政」,背後全是權術
從靖康到退位,趙構用了35年。
這35年,是南宋初期最難熬的時期,戰爭不斷,財政崩潰,百姓動盪,文臣壓軍將,朝廷割肉求和。趙構知道,這攤子太難收場。
所以他精心策劃了一場退位劇。既保住自己「高風亮節」的名聲,又躲過權力鬥爭最危險的爆發期。
趙昚上位之後,很多人以為新氣象來了。可頭幾年,政令依舊謹慎,政策依舊保守。因為趙構還在,他的眼睛還在看。
趙昚不得不左右試探,既不能得罪父皇,又不能無所作為。
南宋最初的穩定,並非趙昚治理有方,而是趙構留下了一套完整的「可控體系」。他布好棋子,交出王冠,卻不交出殘局。
他在退位中完成了一件事:把「趙構的南宋」變成了「趙匡胤後裔的南宋」,但保留了他趙構的影子。
有人說他仁厚,有人說他避禍,有人說他懦弱。
可從史料能看到的,是他退得比誰都果斷,比誰都精明。
他不戀戰,卻處處設防;他不留子,卻設法留下話語權;他不親政,卻通過太上皇身份遙控朝政。
趙構這一招,讓南宋度過初創期的最難階段,卻也埋下權力「軟分裂」的隱患。
這不是一位高尚君主的選擇,是一位理智政治家的算計。
他知道宋朝走不到千秋萬代,能做的只有保住當下。
所以他退。退得體面,退得及時,退得帶刺。
在他退位整整10年後,趙構病逝於德壽宮,終年67歲。他走得安穩,也走得徹底,可他那套「虛退實控」的方式,成了後來太上皇制的範本。
歷史沒留情,只留下一串串軌跡。趙構那個「還位太祖一脈」的動作,看起來是大義,其實藏著太多不得已。
趙構退位,不是傳承,是抽身;不是明哲保身,是精算避禍;不是禮讓三分,而是利字當頭。
誰都知道,56歲不算老,精力也未見衰退。趙構是在做局,把「太上皇」的身份當成第二道護城河。
他退了,但並沒有走。他依舊住在宮中,依舊接見群臣,依舊干預軍政。
他把皇位交出去了,把權力的一部分拿回來。表面上風平浪靜,實則波濤洶湧。
趙昚很清楚這個局,他不上頭,也不反擊,按部就班當皇帝。
太上皇和皇帝兩套權力系統平行運轉,趙構贏得的是體面,也是主導權。
這個安排,至少維持了10年局勢穩定。可趙構知道,時間拖久了,終究會出事。
與其未來被驅逐、清算,不如提前設局、全身而退。他選趙昚,不是親情所至,而是博弈所需。
趙構退得早,只為避禍不為清名
趙構退位前夕,宮裡氣氛很怪,誰都看出不對勁,卻沒人敢說。
那是紹興三十二年,1162年正月,趙構宣布禪位,大臣反應出奇地快,奏章一片歡呼,說「太上皇高風亮節」,說「天命所歸」,說「萬民所盼」。
可真有人信這些?宮門之外,朝堂之上,人人心裡都清楚,這不是一場感情戲,是一場政治演出。
趙構退位有多快?快到不像話。
當天詔書一下,趙昚立刻登基,改元「隆興」。
所有儀式提前準備妥當。宮廷衛隊換防,后妃遷居,禮儀大臣一排排站好。一切都在計劃之中,半點不拖泥帶水。
趙構不是做戲,他是真的怕。
過去十多年,他活在各種刺痛里。建炎年間的軍變,韓世忠、張浚的跋扈,李綱的直言,岳飛的威望,這些人不是敵人,都是趙構心頭的影子。
他在這些「忠臣」身上看到了什麼叫「壓制不住的力量」。
尤其是岳飛。那場殺岳的風波之後,趙構明白,任何一個太有「理想」的人,都會威脅到皇帝的安全。
哪怕是真忠良,也不能留。岳飛走了,可朝野信任也崩了。
趙構從那以後,徹底認清一個現實:只靠皇帝的身份,是壓不住那些人心的。
所以他得退。退得早,退得快,退得乾脆。
趙昚不是岳飛,不是韓世忠,不是張浚,他沒軍權,也沒「北伐夢想」,趙構選他,看中的不是賢明,而是安分。
他知道趙昚不會逼宮,不會清算舊事,不會反咬一口。
趙構要的,不是交出權力,而是把「風險」轉移。
他繼續留在皇宮,仍被尊為「太上皇」,每日早朝前,大臣要先向太上皇請安。軍中重大調令,也要「御前通報」。
趙昚是皇帝,趙構是神,他退了身,卻沒退場。
這種結構,看似穩定,其實危險無比。因為它不是分工,而是牽制。太上皇不走,皇帝難大展拳腳;皇帝強硬,太上皇會幹預。
南宋政壇,進入一種「雙頭權力」的微妙狀態。
趙構也清楚,這種格局拖得越久,越容易出亂子。他必須一步步淡出,慢慢斷線,開始頻繁出行,搬離皇宮,搬去德壽宮,自稱「養病」,減少露面。
可他始終沒有徹底放手。直到去世前,他依舊保持對政局的某種掌控感。
哪怕是趙昚身邊的親信安排,他都有份插手。
趙構退位,不是清高,是清醒。他躲開刀口,卻死死捏住刀柄。
表面風光的「歸政」,背後全是權術
從靖康到退位,趙構用了35年。
這35年,是南宋初期最難熬的時期,戰爭不斷,財政崩潰,百姓動盪,文臣壓軍將,朝廷割肉求和。趙構知道,這攤子太難收場。
所以他精心策劃了一場退位劇。既保住自己「高風亮節」的名聲,又躲過權力鬥爭最危險的爆發期。
趙昚上位之後,很多人以為新氣象來了。可頭幾年,政令依舊謹慎,政策依舊保守。因為趙構還在,他的眼睛還在看。
趙昚不得不左右試探,既不能得罪父皇,又不能無所作為。
南宋最初的穩定,並非趙昚治理有方,而是趙構留下了一套完整的「可控體系」。他布好棋子,交出王冠,卻不交出殘局。
他在退位中完成了一件事:把「趙構的南宋」變成了「趙匡胤後裔的南宋」,但保留了他趙構的影子。
有人說他仁厚,有人說他避禍,有人說他懦弱。
可從史料能看到的,是他退得比誰都果斷,比誰都精明。
他不戀戰,卻處處設防;他不留子,卻設法留下話語權;他不親政,卻通過太上皇身份遙控朝政。
趙構這一招,讓南宋度過初創期的最難階段,卻也埋下權力「軟分裂」的隱患。
這不是一位高尚君主的選擇,是一位理智政治家的算計。
他知道宋朝走不到千秋萬代,能做的只有保住當下。
所以他退。退得體面,退得及時,退得帶刺。
在他退位整整10年後,趙構病逝於德壽宮,終年67歲。他走得安穩,也走得徹底,可他那套「虛退實控」的方式,成了後來太上皇制的範本。
歷史沒留情,只留下一串串軌跡。趙構那個「還位太祖一脈」的動作,看起來是大義,其實藏著太多不得已。
趙構退位,不是傳承,是抽身;不是明哲保身,是精算避禍;不是禮讓三分,而是利字當頭。
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