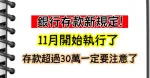7/8
下一頁
婉容與2名侍衛私通懷孕,生下一女嬰,溥儀得知後:一人給400大洋

7/8
「吁嗟親愛的!不知道你心中到底有怎麼感想?不覺令人好恨,絕不該將臣妾嫁與有婦之夫。就說前數年在張園,我總是懷疑你與淑妃很要好的時候,我心中十分悲傷,終日終夜終刻無一時不是悲泣,所以憂思過度,以至經痛和腹瀉一直不停,能有近百天。因此,才有現在的神經衰弱。可是,我也沒有牢騷埋怨過,每天見人時候還必須洗面賠笑,那時,誰也不知道我心中之苦。」
婉容和文繡之間的不和最終結束於1931年8月,文繡向溥儀提出離婚之時,婉容以為自己勝出了,卻沒想到卻是掉入了更深的地獄。
因為離婚的恥辱,再加上溥儀的「復國夢」一直受挫,惱羞成怒的溥儀將自己怒氣發泄在婉容身上,在自傳中,他提到:「自從她(皇后)把文繡擠走之後,我對她有了反感,很少和她說話,也不太關心她的事情。」
生活愈發不如意的婉容更加依賴香菸,她的心態也愈發被苦悶不得志的日子所折磨,信念逐漸崩塌,最終只剩淒涼。
三、私通侍衛,苦痛折磨終瘋魔
溥儀的七妹曾經回憶說:「皇后長得非常標緻,個子瘦高,也有文化,大哥當時一心想復辟,不會把愛給妻子,孤寂與心事忡忡使她變得很古怪……我們都知道,這種家境使她心理已經變態了。」
被折磨了多年之後,婉容的驕傲與底線終是被突破,曾經那個大家閨秀不復存在。
在1932年,婉容前往旅順,與在此任偽滿洲國執政的溥儀會和。
本以為與丈夫的見面可以緩解內心的傷痛,但是溥儀的無視以及日本人的監視更加加重了她的苦難。
在這種情況下,婉容選擇了投入他人的懷抱。
根據溥儀的御前侍衛李國雄在《伴駕三十年》中的記載:
到了旅順之後,後宮的男女大防就鬆弛了許多,皇后和幾個格格也能經常和我們幾個(侍衛)隨便見面了,皇后偶爾還會把我們留在宮中「湊手」,陪她和格格們玩紙牌.....我懷疑她和祁繼忠的私情關係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。
皇后當時睡懶覺,經常日上三竿也不起,溥儀便派我們幾個去請,可派的人無非是我,祁繼忠,李體玉三人。
有好幾次,我到她的寢宮門前,見門故意裂開一條縫,皇后躺在床上並沒有睡。「老爺子該起了,老爺子該起了,皇上讓奴才來叫了。」
我招呼了半天,她也不起,還故意一轉身,把被子帶開,露出半裸的身子來,幾次都是如此,我(苦不堪言),覺得能躲開這個差事才好,祁繼忠和李體玉則不然,他們兩個很積極。
祁繼忠和李體玉,便是婉容的出軌對象,他們兩人在當時都可以說是溥儀眼前的紅人:祁繼忠被溥儀提拔為奏事官,在不久後遠赴日本留學深造;而李體玉則極得溥儀的信任,甚至於在夜晚本應貼身守衛溥儀的時候,他還偷偷去和婉容私會。
後來溥儀回憶道:在「滿洲國」的時候,婉容因為時常跟一個姓李的「聽差」接觸,一來二去,就產生了感情。
為避人耳目,兩人很少當面說話,大多數是通過婉容屋裡伺候她的一個老媽子來相互遞信兒。
當然,紙包不住火,有傭人向溥儀告發了這件事,溥儀截到了兩人互相傳遞的紙條,並在一個夜晚將兩人抓姦在床,而更令他無法接受的是,當時,婉容已經有了身孕。
對於這個孩子的去留,婉容顯出了前所未有地決絕,她長跪在溥儀的身側,提出的要求是,如果孩子生下後,溥儀要承認這個孩子是他自己的;如果不行,生下孩子之後,要允許孩子悄悄在外邊養著。
婉容和文繡之間的不和最終結束於1931年8月,文繡向溥儀提出離婚之時,婉容以為自己勝出了,卻沒想到卻是掉入了更深的地獄。
因為離婚的恥辱,再加上溥儀的「復國夢」一直受挫,惱羞成怒的溥儀將自己怒氣發泄在婉容身上,在自傳中,他提到:「自從她(皇后)把文繡擠走之後,我對她有了反感,很少和她說話,也不太關心她的事情。」
生活愈發不如意的婉容更加依賴香菸,她的心態也愈發被苦悶不得志的日子所折磨,信念逐漸崩塌,最終只剩淒涼。
三、私通侍衛,苦痛折磨終瘋魔
溥儀的七妹曾經回憶說:「皇后長得非常標緻,個子瘦高,也有文化,大哥當時一心想復辟,不會把愛給妻子,孤寂與心事忡忡使她變得很古怪……我們都知道,這種家境使她心理已經變態了。」
被折磨了多年之後,婉容的驕傲與底線終是被突破,曾經那個大家閨秀不復存在。
在1932年,婉容前往旅順,與在此任偽滿洲國執政的溥儀會和。
本以為與丈夫的見面可以緩解內心的傷痛,但是溥儀的無視以及日本人的監視更加加重了她的苦難。
在這種情況下,婉容選擇了投入他人的懷抱。
根據溥儀的御前侍衛李國雄在《伴駕三十年》中的記載:
到了旅順之後,後宮的男女大防就鬆弛了許多,皇后和幾個格格也能經常和我們幾個(侍衛)隨便見面了,皇后偶爾還會把我們留在宮中「湊手」,陪她和格格們玩紙牌.....我懷疑她和祁繼忠的私情關係就是這個時候開始的。
皇后當時睡懶覺,經常日上三竿也不起,溥儀便派我們幾個去請,可派的人無非是我,祁繼忠,李體玉三人。
有好幾次,我到她的寢宮門前,見門故意裂開一條縫,皇后躺在床上並沒有睡。「老爺子該起了,老爺子該起了,皇上讓奴才來叫了。」
我招呼了半天,她也不起,還故意一轉身,把被子帶開,露出半裸的身子來,幾次都是如此,我(苦不堪言),覺得能躲開這個差事才好,祁繼忠和李體玉則不然,他們兩個很積極。
祁繼忠和李體玉,便是婉容的出軌對象,他們兩人在當時都可以說是溥儀眼前的紅人:祁繼忠被溥儀提拔為奏事官,在不久後遠赴日本留學深造;而李體玉則極得溥儀的信任,甚至於在夜晚本應貼身守衛溥儀的時候,他還偷偷去和婉容私會。
後來溥儀回憶道:在「滿洲國」的時候,婉容因為時常跟一個姓李的「聽差」接觸,一來二去,就產生了感情。
為避人耳目,兩人很少當面說話,大多數是通過婉容屋裡伺候她的一個老媽子來相互遞信兒。
當然,紙包不住火,有傭人向溥儀告發了這件事,溥儀截到了兩人互相傳遞的紙條,並在一個夜晚將兩人抓姦在床,而更令他無法接受的是,當時,婉容已經有了身孕。
對於這個孩子的去留,婉容顯出了前所未有地決絕,她長跪在溥儀的身側,提出的要求是,如果孩子生下後,溥儀要承認這個孩子是他自己的;如果不行,生下孩子之後,要允許孩子悄悄在外邊養著。
 呂純弘 • 5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